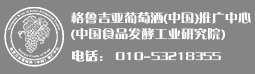作者: 發布時間:2017-08-29 關注度:221
無硫有機釀酒之風起源于法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位名叫馬賽爾?拉皮埃爾(Marcel Lapierre) 的年輕人和他的朋友們掀起了這場風潮。而在格魯吉亞,引領葡萄酒革命的并不是年輕人,而是長者,至少是中年人。當蓋拉找到約翰的時候,已經30歲了,雖然不算老人,但也不是小伙子了。這股釀酒工藝復興的浪潮,正是由那些夢想被迫擱置的人們推動,他們的年齡介于30歲到70歲,勇敢推動著改革的步伐。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開創了振奮人心的葡萄酒新時代,推廣有機酒,號召人們摒棄化學添加劑。可以說,這場反對化學添加、不走尋常路的葡萄酒革命是一場鮮有年輕人參與的戰斗。
慢食組織 (Slow Food)成立于意大利,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保護地區特色烹飪方法與傳統農業。該組織在格魯吉亞設有分支機構。索立科與其負責人拉瑪茲(Ramaz)見過面。拉瑪茲身材健壯,頗有主見,聲音有些沙啞,而且他也釀酒。兩人價值觀相似,一拍即合。他們隨即開始四處網羅同樣熱衷傳統工藝,能釀造優質天然有機酒,并愿意推動市場的人才。他們就像葡萄酒傳教士一般,共同努力,最終將創建一個龐大的網絡。
迪蒂米(Didimi)已年逾七十。老人家的肖像被印在酒標上,并注有“我是迪蒂米,這是我的卡胡娜葡萄酒”的字樣。這款酒首次在意大利市場銷售。還有一位老人叫蓋奧茲?蘇普奧馬茲 (Gaioz Sopromadze) ,六十多歲,似乎由于過多食用khachapuri 芝士面包而挺著大肚腩。他用莎卡維拉 (Chavkeri) 葡萄釀出了如今非常受歡迎的酒。2013年,他首次去法國推廣自己的葡萄酒。我在巴黎的一場品酒會上認識了他。那時的蓋奧茲正沉溺于風姿綽約的巴黎美女之中。對此,他不以為然,辯解道:“她們實在太漂亮了!”。那周晚些時候,我與他在盧瓦爾河谷一間漂亮的酒窖里見面,在場的還有另外幾位格魯吉亞人。酒窖很深,儲藏了不少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好酒。蓋奧茲當時有些憤憤不平:“我祖父曾有三公頃葡萄園。1921年之后,所有的東西都被奪走了。”他非常激動,似乎這事就發生在不久之前。“他們瓜分我們的產業,搶走了我們的土地,分給了什么都不懂的人。他們掠奪我們的酒窖,里面收藏的好酒就跟這里的一樣。”他冷笑著,繼續說道:“我討厭前蘇聯,討厭蘇聯共產黨。”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無論是紡絲工人還是釀酒師,他們渴望在自己的領域出人頭地的夢想,被前蘇聯擊得粉碎。而如今,一切都有實現的可能。老人們又重新充滿激情。雖然蓋奧茲只有0.75公頃土地,但他已經在著手購置新的葡萄園。他這把年紀了還要重新栽葡萄?葡萄藤幾年都結不了果,這樣的付出還有意義嗎?這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樂觀精神啊。而在格魯吉亞,精神追求深植于人心,人們對長遠夢想的奮斗也從未停止。
午餐的香味從索立科的房子里飄散出來,美食已經擺放在一棵櫻桃樹下的餐桌上。索立科的妻子尼諾加入我們,聽著我們對她廚藝的夸贊。餐桌上擺著油炸餡餅、各式蘑菇等。還有一道雞蛋做的美食,非常好吃,雞蛋像是來自被施了魔法的母雞。我們品嘗著索立科的年份酒。這時,他舉起 2006 年卡斯泰利葡萄酒,動情地說:“這是我的摯愛。這就是我。”
四個小時后,我們的人數增加到六個,午餐仍在繼續。在格魯吉亞,午餐很容易就被拖延到下一頓開餐。盤子逐漸堆積如山,已經蓋滿了白色的桌布,這也是當地的習俗。家里有客人時,每頓飯都是大餐,都是一場饕餮盛宴。盡管我已經撐得像頭牛了,但也不能停下來喘口氣。因為之后,另一位釀酒師又要帶我趕往下一個目的地。
告別時,我倚著門框看索立科幫尼諾清理餐桌。他們一邊忙活,一邊唱著多聲部歌曲,這旋律在其他國家從未聽過。我突然意識到,多聲部音樂不僅僅是像約翰妻子凱特溫的Zedashe那樣的藝術團所做的娛樂表演,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旋律與歌聲層次分明,恰似極富層次感的葡萄酒。這種歌唱的藝術,以及萬物多樣化的理念,已經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
卡哈?貝爾什維利 (Kakha Bershivili) 帶我到他家。由于他完全不懂英語,便找來他女兒的朋友當翻譯。卡哈是一位素食主義者,也是小提琴藝術家。他還盡可能地在葡萄園耕作,也釀葡萄酒。他堅定地支持天然酒,同時他也加入“青春雖逝,葡萄酒革命不老”的隊伍中,復興傳統工藝。我們在特拉維市下車,拾級而下走進喧囂的市場,找到菜攤,買了一公斤蘑菇以備晚餐用。
當晚,參觀完卡哈的葡萄園和酒莊,并沿河邊散步返回之后,大家便開始忙著做飯,在走廊喝酒。夜色漸濃,胡狼的嚎叫與青蛙,昆蟲的叫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我從未聽過這么持久不息的蟲鳴聲。臨近夏至,自然界一片生機。
談話中,我逐漸對這個20 來歲的翻譯產生了興趣。他也是一位釀酒師,希望在學完釀酒專業后,能有機會去新西蘭和勃艮第實習。
“你想去哪兒工作?”我問道。
他想在格魯吉亞或其他國家的大酒廠謀一份職。
“真的嗎?”我很驚訝,“但今天聽了這些故事,喝著這些酒,難道你對這種特殊的釀酒技術一點都不感興趣嗎?”
他笑了。他說,他也喜歡這種酒和它的口感,但他補充道:“這樣釀酒太辛苦了。”
“辛苦?那些比你年長幾十歲的前輩都沒有抱怨,你怎么能喊累呢?他們都不怕累啊。”我說道。
這個年輕人生于前蘇聯解體之后,沒有經歷過生活的艱辛。他無法真切體會年少懷才不遇,中年方能施展拳腳的感受。想到這兒,我有些難過,我想到那天深夜我和尼基在第比利斯,與烹飪學校的那個家伙爭論的情景,當時的感受與現在一樣。清洗Qvevri陶罐的確很辛苦,但格魯吉亞人還怕苦怕累嗎?
“你就想多掙錢。”我責怪他,他溫和地笑了。
我們喝著2009年的好酒和第一批2006年份酒,我問這年輕人:“你可以找一份大酒廠的工作,但是你釀造自己都不愿意喝的酒,晚上能安心睡覺嗎?難道你不想像卡哈一樣釀出好酒嗎?”喝著新酒老酒,我們開始吃蘑菇。我吃著美味的西紅柿餐,開始擔憂格魯吉亞的未來,如果年輕一代不愿像老一輩那樣埋頭苦干,那么工業生產會不會取代傳統釀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無疑將是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