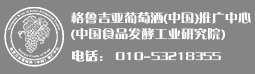作者: 發布時間:2017-11-10 關注度:157
格魯吉亞宴會上的美食不斷,賓客們也絡繹不絕,有丹麥的侍酒師,還有好些美國人。在場的還有日本攝影師:池田嬌小活潑,惠子高挑嚴肅,他們都癡迷于天然葡萄酒和格魯吉亞葡萄酒。當然還有尼基,我有段時間沒見到這位“黑色電影的明星”了。他一直忙著修建 marani 酒窖、采收葡萄,常常忙碌到天亮。我擁抱他的時候,甚至能感覺到他身上的骨骼。他的身體就像是一個永遠都填不滿的鍋爐。
“陶罐已經埋進地里了嗎?”我問。
他沮喪地搖了搖頭,輕聲回答道:“還沒有。”
“但是大家都摘完葡萄了。”我說道,不禁為他擔心。
他聳了聳肩,抬頭望向天空。我猜,他這是聽天由命了。
“你明天去梅斯赫基(Meskheti)嗎?”
“對!”我回答。
“我也去。”他說。
“但是你還要收葡萄啊!”我回答,心里卻在想:這次旅行將要變成一場路上的派對了。太棒了!
“沒事,不用擔心。”他說。
這時約翰把我拉到一邊,問我是否介意日本攝影師加入我們的旅行。
“當然可以。”我回答道。如同《狂野西部 (Wild West)》(譯者注:音樂名)旋律的康加舞,我們按著自己的節奏,約翰帶路,駛向格魯吉亞的“狂野西部”。在格魯吉亞就是這樣,無論是 Supra宴會上還是旅途中,隊伍都會不斷壯大。
我們停下來,品嘗這原汁原味的酒,還有美味的茄子。濃濃的香味中透著絲路各國香料的異域風韻。酒意正酣時,一個角形酒器被端上來。在格魯吉亞宴會上,除了常見的淺底陶碗和玻璃杯,第三樣容器-羊角酒杯也必不可少,酒杯在賓客間傳遞,猶如印第安人使用長桿“和睦”煙斗。這個喝酒容器乍一看就像我爺爺在猶太教贖罪日吹奏的兩端開口的號角,但不同之處在于,它是一端密閉的。羊角杯大小不一,而約翰則把最大號的拿了出來。見此情景,我懵了,這樣喝豈能不醉?縱使喝的是天然葡萄酒,也難以招架啊。
我們的酒司令約翰站起來敬酒。他對著夜幕中滿面笑容的年輕姑娘卡米爾說:“這杯要敬我們的傳統,向不忘傳統、引領變革的卡米爾的父親馬賽爾敬一杯。”說完,猶如俄羅斯人喝伏特加一口悶那樣,約翰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按照阿拉韋爾迪輪流祝酒的風俗,格拉起身繼續發言。“我祖父能釀出好酒,因為他有一顆開放的心。他心底坦蕩,夜里睡得香。我不會釀造像毒藥一樣難喝的葡萄酒。我會像祖父一樣,為人們奉上純天然美酒。馬塞爾·拉皮埃爾做到了。他雖然已經過世,但是他的孩子們會繼續他的事業。我們會愛你的父親,繼續他未竟的事業,回報世人。卡米爾,這將是你未來的生活。在此,我首先要借這杯酒,緬懷你的父親;二來希望你繼承你父親的遺志。子承父志意義極為重大。我經常問自己,我的葡萄園和Qvevri陶罐釀酒事業能否后繼有人?孩子們愿意學這門手藝、喜歡這樣的生活嗎?”
最后,羊角杯傳到了約翰的妻子凱特溫手中。“我要喝掉這杯酒。這里面裝的是葡萄酒,更是真理。”她如此說道。雖然我不太明白她所說的話,但她說話時深色的眼睛里滿是威嚴,我對她也沒有絲毫的懷疑。接著酒杯傳到了我手里。我站起來,拿起羊角杯,倒酒。酒并沒有倒滿,但愿沒人看到我耍的小聰明。我一時想不出像他們說的那么好的祝酒詞,好在我還有秘密武器,“為了格魯吉亞,干杯”,我一飲而盡,然后把羊角酒杯傳給下一位。
美酒醇香,夜色醉人。加利福尼亞人拿出吉他,開始歌唱真理,動情而又投入。的確,格魯吉亞就是有這種感染力。不過我對他還是有些警惕。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人試圖玷污純潔,自打人類開始直立行走之日起,就存在這個問題。十九世紀下半葉,引領格魯吉亞民族復興的圣人伊利亞·查查瓦澤 (llia Chavchavadze) 就堅決捍衛自然葡萄酒,他曾寫道:“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我們創建一個只有純正葡萄酒的世界!”
我打量著這個加利福尼亞人,心里想:有些人就是這樣在贊譽品德的同時又要破壞它嗎?
拉瑪拉使我意識到,這個加利福尼亞人就是那只狼,對格魯吉亞這只鹿虎視眈眈。這樣的人只會讓天然酒釀酒師們更加智慧,更加堅定,更加專注于自己的事業。就像在愛情中一樣,人要相信直覺。我的直覺告訴我,在格魯吉亞,家人們住在同一屋檐下,或者至少周末團聚;在宴會上,人們必定要緬懷逝去親的人,祭奠被烈士鮮血浸染的大地,銘記國家的歷史與真理。在這樣一個國家,這份厚重的葡萄酒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足以抵御外界壓力,與現代化和變革的潮流逆向而行。這讓我想起當我苦苦尋覓一件放錯地方的東西時,一位朋友曾對我說過的話:是你的就永遠不會丟。